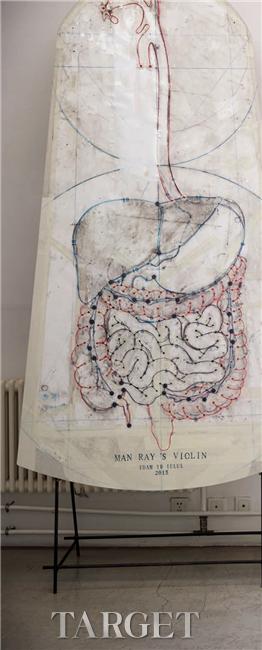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而流动,陆垒的父母以技术员的身份从东北来到江苏连云港支持当地的一个化工企业。也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片《中国》,这部拍摄于1972年的电影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一年,陆垒出生,在具有时代特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童年记忆成了陆垒不断探寻的灵感源泉。金属板、钢筋、混凝土是他创作常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构建出一种极具20世纪后期视觉特色的氛围,粗粝的质地以具有压迫感的体量传达着集体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感官体验。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充盈的年代,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中国人的脸上展示着一种沉浸式的表情,那是一种被信仰支配的样貌;那也是一个匮乏的年代,想象力属于集体和国家—在一个画抽象画被认为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起码个人没有机会像那天的采访一样谈论这些不太实用的话题:

—在你的作品中,什么是重要的?
—嗯~,我说不好。
—细节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但是这跟要表达的核心关系不大。
……
关于艺术创作,一个经典的命题是“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用做出来”。陆垒没法说明自己做的是什么,他将自己的经历、经验、学识、体验灌注到作品当中。2019年11月,香格纳画廊上海空间展出了陆垒个展“荒唐小说”,以浪漫的想象构建了“漫游的巨人的狂想”。

巨人有多巨?宇宙星辰。一进展厅,一套沙土翻模的浪漫宇宙散落在眼前。《在寒冬,巨人们聚集在广场中心,用沙做的圆球按照星辰的方位,玩一种弹球游戏》,几乎没有人用这样的一长串陈述句作为作品的标题,而陆垒这么做了。沙土混合大量的胶,做成“弹球”,若以其中太阳的大小作比,这些“弹球”就是星球。展览的作品配合着标题“荒唐小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毫无疑问,在集体主义的年月,国家叙事所推动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在一个接着一个五年规划中快速实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现代启蒙逐渐从文学化的想象落实到日常生活,理性的个人意识被唤醒—我们欣赏伟人豪迈的气魄,而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更加具体和务实。“巨人”纵可飞天揽月,但总脱不去天方夜谭的神话情节。那些粗粝的沙土在摆布和挪移中甚至松散掉落,不禁让人怀疑巨人的体量是否是由这样稀松的质地构建。时间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令世界瞩目,GDP背后是国人理性的觉醒。回顾往日的“巨人”难免觉得荒唐,“寒冬”“巨人”“广场”“中心”“弹球”这些意象可不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过往的理性反思?洒落满地的形式就是答案。

中心对称是一种庄严的形式,是平稳的、平衡的、向心的形式。这种常被用于纪念碑和大型建筑的对称样式也被陆垒用在了《圆括号长廊与卫生池》上。铝板搭建的两个半圆围挡(圆括号)环绕着一个圆形的水池,尖形的雕塑正是向塔特林“第三国际纪念碑”的致敬。在铺满瓷砖的圆形舞台上,欧松板基座将这个庄严造型的旋转水池高高托起,由上世纪末中国人日常生活所构建的丰碑被仪式化地陈列于展览的最后,为巨人的小说画上一个句号。螺旋的水道在视觉上引导着纪念碑向上的升力,如果没有水龙头的凸起,长时间的观看甚至会给人造成一种旋转的错觉。而恰恰这些凸起不是别的,是专门供水的水龙头。流水的细节也令人印象深刻,从稀稀拉拉到滴滴答答,水流的几种状态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水压不足是常有的事,坏了的水龙头又得不到及时的修理,关不严。

在“小说”的框架之下,这件作品是最直接、最具体,可能也是最荒唐的一件。从被日常磨砺的麻木中跳脱出来,回望那个匮乏的年代,艺术家以细腻的感受力重新发现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将之放大到纪念碑的体量,并用崇高的形式装修了整个场域,赋予这个细节以超越性的意义。水滴汇成水流顺着水槽流下来,在观众视线的高度初具规模,哗哗流淌的效果在视觉上形成了一股向下的力,牵制着尖形纪念碑上升的趋势。这是视觉形式的张力,也是意义上的张力,举重若轻,个人的奉献汇聚成历史的洪流一去不返,结晶成丰碑的集体奉献永垂不朽。

在目不暇接的信息轰炸中,那些日子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今天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能力,用信息代替感受,滔滔不绝。陆垒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创作跟不上新闻的速度,“少则得,多则惑”,那个老式水龙头以50年前的方式滴水,不同的是,展厅柔和的灯光和作品纪念碑的形式无不强化着这个细节,它以一种历史感的节奏唤醒中年人的记忆,那些物质匮乏的时光在心灵深处重新闪光。

与陆垒见面的场景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树荫、清风、思考、对谈,一种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已经全然取代了那个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中国。今天我们拎着名牌包,涂上网红口红,从短视频平台上获取消息,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无比富足的生活却处处充满了焦虑。对意义的不断追问可能是陆垒将创作视为荒唐的原因。“现实比艺术更刺激”,那些刻意制作的形式远不能对抗生活的强度,好比那个被忽略在日常中的水流,放在展厅中却倍加感人。回望匮乏,陆垒的创作是要声讨那个逝去的时代吗?也许不全是,我们从这些粗粝的质感中看到了艺术家打磨细节时的满足。





